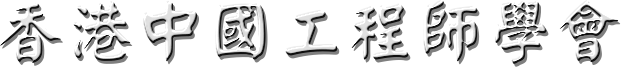“大禹治水”的21世紀新辯釋
(香港) 楊偉國博士 (科學技術哲學專業)
自從2002年在香港摩囉街古董店翻出一件並不太起眼的長方、四足青銅器(且一足有缺口,又缺失了上蓋、垂環只剩下一個),但總算是周代較古舊的一種食用禮器──“盨”(讀作【許】 xǔ)。這件不是破土掘出、殘破、銹蝕的禮器,更可能是一“贗品”。臺灣的業內人士曾光顧、察看過,但沒有購意。
有心人士購入後,送到北京有關部門進行鑒定。經考古學家仔細清理了全部土鏽後,發現在其器皿內底有10行、約98字的銘文。銘文中有“遂公曰”三字,被敲定為遂國物品,被冠為“遂公盨”〔注1〕。遂(古字為“燹”)國是在今山東,虞舜之後,春秋魯庒公十三年(西元前681年)被齊所滅。
下面銘文的釋讀,儘量用通用的文字:(有關注釋請參閱後面附文)

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
差地設征,降民監德,乃自
作配鄉(享)民,成父毋。生我王
作臣,厥沫(貴)唯德,民好明德,
寡(顧)在天下。用厥邵(紹)好,益幹(?)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籲明
經齊,好祀無[貝鬼](廢)。心好德,婚
媾亦唯協。天厘用考,神複
用祓祿,永禦于寧。遂公曰:
民唯克用茲德,亡誨(悔)。
銘文多個字,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對於古奧的銘文來說,看法有異是正常的。
“遂公盨”銘文記載有大禹治水的歷史事件,其行文方式與後世不同史家的記錄多有接近。過去,在青銅器上只出現過簡單的“禹”字,並無細節。此物品的出現是有關大禹治水的最早文字例證。80年來顧頡剛先生掀動的“古史辨”學術運動,論說“禹”是一條“蟲”。現可以說是有一個恰當、終結的回答了。
筆者研究信息哲學,從諸多資訊中理出不少的新知識。21世紀信息資訊時代的新思維,讓我們對大禹治水涉及的文化、社會、科技等問題,作一些大膽的新辯釋,本文亦可為《香港中國工程師學會》新網頁啟動的一項獻禮。
一. 大禹治的水是從何而來
二. 夏禹族人原居地在何處
三. 夏人有超前的天文知識
四. 夏族言語不是一音一字
五. “禹傳子”的生物學意義
一. 大禹治的水是從何而來──可能是“海浸”
大禹紀念歌的歌詞:“大禹治水,洪水滔天,神州無淨土!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所以大禹一直被國人尊為中華工程技術之祖。

中華甲骨文字的出現于殷商,周代的甲骨上亦發現一些體形更為精細的文字符號。夏代的陶器上只有一些極為原始的刻劃符號,所以,有關夏代的歷史只能從周代、商代史家文人的間接描述,尋找其中的片言隻字,才可發掘出有價值的歷史真貌。
有關大禹治的水,《孟子》篇中兩次提及“水逆行”。大家對中國地理有些認識的話,清楚知道中國地勢西高東低,黃河、淮河、長江都是由西流向東。歷史上的江河氾濫,洪水均由西向東湧來的。為什麼孟子反復地陳述“水逆行”!
古地質學家發現江蘇、浙江一帶在5,500年前曾經歷過一次嚴重的海侵,海水淹沒了大部份土地,使得著名的良渚“玉文明”自5,500年前突然消失,大量具有古夏特色的夏代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廣泛展開。玉琮上的神面──饕餮,成為夏代玉器的一個重要標誌。各省都發現有古夏的文化遺跡,他們都渴望能被評為古夏曆史的發源地,但終究未被傳統的歷史學家所接受。
電影《2012》就是描述未來可能出現的最大的海浸災難片,中華民族還是未來大海嘯災難的拯救者。筆者在觀賞時,大腦意識飛越了5,000年,回到堯舜治水年代。筆者在殯儀館靜看道士演繹“買水”程式,他們盛裝而有板有眼的走着“禹步”(相傳是數千年前大禹治水特有的跛步),攀千山、涉千水;過金橋、跨銀橋,千辛萬苦要為先人達成心願,在海浸鹼地上端出珍貴的“淡水”,為死者沐浴禮祭!回憶到東南亞觀看的民族舞蹈表演,兩者同是被遺忘的歷史陳述。
二. 夏禹族人原居地在何處──可能是南方江浙一帶
正因為這次水災連續多年(以百年算),海浸才逐步退去。但是土地已不適宜種植糧食,只可種植不怕鹽鹼的棉花。7,000年前的河姆渡水稻文化、5,000年前的良渚玉文化,被古越夏人帶到北方去。背負着有較優秀古越文明的夏族人,雖然廣布中華大地,新移民肯定會與原居民有爭鬥的。夏族新移民較集中居於現今山西南、河南北部一帶,以“河洛”為核心,4,000年前建立後來的夏王朝。
從現代中華民族50多個族群的DNA差異細緻的分佈知道〔注2〕,在5,000多年前由南北兩大族群開始(約以北緯30゚-35゚為界),經過多年的民族大遷徙,形成了現今多個族群的地區分佈。從DNA的微細變異中,更可推測其交流轉變的年限,民族的大遷徙可以從現代生物科技DNA中得到堅實的證據。
南方漢族和南方少數民族血緣關係較近。在雲南的少數民族中,保留着更遠年的華夏古越族的DNA原始結構。在海浸大水災後,他們可能遷徙至更偏遠的山區定居後,血緣較少與其他族群交流。
在北方漢族人群中,亦可覺察到其中不同地區的DNA些微明顯的變化。其中有令一人費解的地方:北方漢族竟與北方少數民族血緣亦相近,甚至是同一源頭!最近剛公佈的蒙古考古新研究清楚地解開這一疑謎:東北一帶的遊牧民族亦是早年來自古南方,多年遷徙北方後,一段時間仍過着農耕社會;後來天氣變壞後,把農業知識轉變為畜牧業,才成為遊牧民族,更被中土漢人稱為外族。
這種變化同樣反映在民族“膚紋”分析上。學術上的膚紋研究包括指紋、掌紋和足紋。特別在現今運動員的挑選中,膚紋的科學研究起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三. 夏人有超前的天文知識──最早“置閠”和記錄了“南門”星
《夏小正》是後人記錄夏代奉行的天文曆法書籍。從這本書中描述的星象運行,夏人曾經使用過一年有十個時段(不是現今概念的“月”),又使用天干地支來紀時的歷時系統。殷商、周人曾經打算放棄夏族的禮制(主要是天文曆法、正朔),但最終周人還是要回復使用夏禮!《爾雅.釋天》有關年歲說:“夏日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現今大眾只留有年和歲的概念,不再用祀、載。“載”多在詩詞歌賦中為了押韻而使用,我們亦清楚它是“年”的另一種表達。
為什麼商周期間會出現曆法上的大變動?
雖然夏人使用十月曆(每“月”有36日,一年36x10+若干天的過年日),他們早已使用置閠方法配合農作規律。但是,殷人重鬼神、嚴拜祀,認為清晰夜月的明缺就是最有效的曆法標準,放棄了夏人曾流傳的紀時系統。再經歷數百年後,時差、歲差的變化已經直接影響到日常的農耕時節。周人建國後,最終還是要接受夏人的原有曆法大框架,只是再給予一些小修訂。所以中華曆法不能稱陰曆,一直被尊稱為“夏曆”、“農曆”,因為它是世上準確的一種陰陽合曆。
近世一位歸國學者鄭文光,從甲骨文中的“天干地支”22個字元構圖進行細緻的推敲。若然對天文有一些瞭解,“子”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個極完美的獵戶座星區構圖!〔注3〕它代表着夏族的參星“子”,居十二支之首,最先使用這套系統應該是夏人。他根據天文歲差的科學計算,“子”參宿一(獵戶座ζ)現時天文赤經與古代赤經差距是3時20分,當年“參”作為古夏族的“大辰”,“子”為春分時應在西元前2100年,經數百年的天文歲差推移之後,怪不得商代紀時的“大辰”要另選“大火”了,這合乎星體運動的天文計算結果。
獵戶座星區構圖 ──甲骨文的“子”字,是全天最為獨特的構圖,美國天文愛好者做實驗,證明連鴿子也可在夜間以此為方向目標的參考圖形!古夏人就是把它描繪下來,作為時間的第一個標誌──5,500年前已出現的夏文字標記!
在《夏小正》中更記述了一顆殷人、周人不可能見到的南方星宿──南門!
此星在天球的南緯60゚,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北方族群是不可能看到這一顆星宿的!生活在長江更南(北緯30゚以南)的人士才可有機會看得見。古夏人是原居住在南方的民族,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據!香港當然容易看到“南門”星。
四.夏族言語不是一音一字──典型的南方古越言語
正因為“周複夏禮”的原故,周人把原先(約800年至1,000年)的“子”時復位為“大火”星。千年的星空推移,夏人的“子”圖像只保留在甲骨上了。從發掘出土的甲骨片,“天干地支”22個字元有準確的刻劃,它們是夏人遺留下來的文化珍寶。從文獻上知道,夏人的天干地支22字元的讀音不是一音一義的,後人以一音一字的漢字元記下夏人的“子”為“攝提格”或“提格”等等。
曾經有夏族居停的地方都留有夏語言痕跡,不少地名保留了極濃厚的古越言語特色,這是另一個明顯的證據。唯一記錄了當年古越人語言的《越人歌》,是春秋時代楚國令尹請專人用漢字記音保存下來極為希罕的文化資料。
近年有學者把《越人歌》與壯語進行比較〔注4〕,首先根據音韻學家對漢字的上古音擬標出每個漢字的中古(隋唐)和上古(周秦)音,然後與壯語、侗語逐一對照,得到古越語與現今少數民族壯、侗語言有較相同的語源關係的結論。
著名廣東學者羅香林教授80多年前已有詳盡的研究。〔注5〕夏言語中對人的稱謂是把尊稱在前、名字在後(後羿、帝昌、胡人安祿山、廣東人稱阿某阿貴等等,都是對男性的尊稱;在911事件後,美國發表的通緝名單中,字頭多有Al.., Ar.., An.., Ab.., Ap.., 等等,它們就是韃靼人安、阿的音轉,這是古夏人對男性的尊稱,夏言語化石中的一種重要痕跡);而且夏言語有明顯的多音節口語,小部份仍然可見在南方的地區方言中;言語文法的倒裝結構亦有獨特之處。
夏族定居河洛後,自稱為“河洛”人。現今廣東、福建一帶說的“鶴佬”語,“鶴佬”兩字就是上古語“河洛”的音轉。筆者就是海豐“鶴佬”人,我們的“男”字讀作“打甫”,“女”字讀作“乍姆”,“盲”字讀作“斜咩”等等,仍然保留著夏族古風。臺灣呂秀蓮曾說過:台語(即“閩南話”、“鶴佬”語、“福佬”語)要比現今“普通話”更為遠祖。她曾要求把台語定為“國”語。
五. “禹傳子”的生物學意義──父代良好DNA的作為
夏禹傳子,中華姓氏由此起。《禮記》中陳述了當年夏代的多種婚姻禮制,它是中華封建制度的重要基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禮教的主要對象。
現今生物科技的知識,讓大眾均知曉:DNA染色體中的X-Y因數,對嬰兒性別變化所起的關鍵作用。子女的性別是由父親的Y因數決定的。因為母親的性染色體中只有X-X,父親的性染色體中為X-Y;若果父親因數中的X與母親的任何那一個X結合,結果一定是一個女性嬰兒。只有當父親精子中的Y因數與母親卵子中的任一個X結合,才可以產生男嬰!
多年前香港在建造大嶼山“360纜車”時,旅遊家李樂詩博士為工程建造引入了南美的騾作為運輸工具,解決在極陡峭的山路上的物料輸送。大家都知道:騾是馬與驢的雜交品種,沒有生殖能力。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一度被列為軍事物資,而全世界懂得大批生產騾的地區是中國與智利。
“馬照跑”是香港的重要口頭格言。大眾對於“馬”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馬算是一種奔跑速度最快的反芻類動物,性格純良,以草本類為食糧。
馬場上的馬約有1,600-2,000磅,約可負載約10-15%體重的騎師進行賽跑。但是,若一位體重150磅以上的騎師(連同馬鞍就不輕了)在馬上用力奔馳,跑不遠,馬要嘔白泡、氣絕身亡!所以,騎師體重都只能選120磅以下的。總的來說,負重並不是馬的強項。而且,馬的食糧講究、容易染病,這是馬的另外弱點。
驢可以負重約15-25%,中國北方農村以驢為重要的畜牲,驢肉亦可口。
騾竟可以負重約30-35%!而且粗食雜糧,極少染病!體型雖比馬、驢細小,早已在中國農業社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如何育出良好的雜種騾,是農業社會中的重要生物科技知識。《齊民要術》中詳盡記錄了育騾的各項要訣。從育養騾的經驗知道:要育出良好的騾,一定要選擇好體健的父輩驢,才可得好馬騾;騾的古字就是“贏”、“鸁”,得利之意,讀音為“盈”。原來更古老的字為吂月丮三字合成,後在其中添上“女、貝、果、馬”等成為一系列形似音同的不同字。
有關中土人士認識“騾”這一雜種動物,原來還有一個曲折的過程。太史公司馬遷曾記錄這是匈奴的奇畜;抱樸子更云: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
南方少數民族倒有長期利用“騾”作為有效的運輸工具的歷史。中原人士見他們經常騎上這奇畜隊伍,牠又能負背超重的貨品,就問是什麼畜物,少數族群稱“lo”。因此,南方族人被稱作“倮倮”;又因為他們常裸體,具倮亦解裸。彝族學者劉堯漢對彝族文明作了深入廣泛的發掘〔注6〕:十月曆、二進位、雜交騾等等均可追源至遠古彝族文化的起始。他對傳統中華傳統文化中的36與72兩個成數,作了深入、認真的分析。這是十月曆、雌雄兩季的深藏內容。一年五個季,每“月”為36日,每“季”自然是72天了。一雌一雄就是一季。另外他認為彝族早已掌握雜交騾的生育技術,歷史要追索到大水災年代,“lo”又是彝族對虎的稱謂。“lo”亦成為後來中土對騾的正式讀音,放棄太史公的早期觀念。
人類的兩次出現美洲:一是在12,000年前白令海峽成為陸橋時,由亞洲大陸北部進入美洲北部的愛斯基摩人;另一次約在5,000年前跨海進入美洲南部的印加古人,衍生成為帶有亞洲血緣的南美族群。他們亦懂得驢馬雜交得騾!美洲與中國對騾的讀音都近“lo”!有學者論述南美洲最早的移民為亞洲古越族人,他們與夏族同源,甚至說是蚩尤的後代,他們把“騾”的知識帶到美洲。
筆者大膽猜想:夏禹治水,不管是河水或海浸,一定要以畜力運輸才可解決工具、石材、食糧、人口等問題,只有騾才可勝任。良好的馬騾要選擇健碩的父輩。從這一生物學的知識經驗中知道,優越父輩的子嗣亦可繼承大業的!
當夏禹治水獲得認同,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大好江山要傳給誰人,再次讓賢推舉嗎?禹選擇了要傳親子了。中國從此有了“姓”!建立了人類嚴謹的中華婚姻制度,防止因族內婚姻而常常出現在類似歐洲王族中的多種遺傳病。
注釋:
1. 李學勤, 遂公盨與大禹治水傳說http://www.cnxia.org/html/14/2007912756.html
2. 趙桐茂, 人類血型, 《科學》, 40卷1期28-33,27頁
3. 鄭文光, 《中國天文學源流》, 1979年 (近年臺灣同名印刷本書出版)
4. 陳國強, 百越民族, 《科學》, 32卷2期31-38頁
5. 羅香林, 古代越族考,《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民國22年(1933) 一卷二期羅香林, 古代越族方言考,《廣東文物》民國29年─兩文存于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6. 劉堯漢(彝族), 《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3

附銘文解釋
這段銘文引用內地學者的介紹,
釋成今文,其大意為:
上天命大禹布治下土,隨山刊木,疏浚河川,以平定水患。隨之各地以水土條件為據交納貢賦,百姓安居樂業。大禹恩德于民,百姓愛他如同父母。而今上天生我為王,我的子臣們都要像大禹那樣,有德於民,並使之愈加完善。對父母要孝敬,兄弟間要和睦,祭祀要隆重,夫妻要和諧。這樣天必賜以壽,神必降以福祿,國家長治久安。作為遂國的國公,我號召:大家都要按德行事,切不可輕慢!
“遂公盨”的這篇銘文,一反其他青銅器銘文的老套,以大禹功德為範例,寫出君臣要為政以德、民眾要以德行事的一篇有論有據、有頭有尾的政論文章。這不能不讓今人折服和震驚!更讓人震驚的是,銘文中的觀點乃至言詞竟和七百年後的《尚書》、《詩經》等古典文獻相一致!此前,人們對古帝大禹及大禹的功德是有所知曉的,因為傳世文獻《尚書》、《詩經》等都多有記載。
經孔子編序的《尚書》“禹貢”篇開首即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即。大禹布治大地,沿大山砍木為記,確定各州名山大河。孔夫子為該篇作序時,也使用了“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的詞句,說大禹沿山砍木為記,疏通江河,劃分九州,依據土地條件規定貢賦。
《尚書》的“益稷”篇更是記述了大禹治水的具體情況,文中再次出現了“隨山刊木”字句,關於“德政”,《尚書》“大禹謨”篇中記載了禹本人的高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意思是,君主的美德在於搞好政事,政事的根本在於養護百姓。修水利、存火種、煉金屬、伐木材、開土地、種五穀,還有抓教育、厚民生、促和諧,這九件事要常常講。
應該說,《尚書》這部中國最早文獻對大禹古帝的記述,相比對堯、舜古帝的記載,是最多的。禹因有“治水大德”,才稱之為“大禹”。《尚書》肯定了大禹開創夏朝的歷史地位。
可是,西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尚書》等經典文獻被付之一炬,後來出現的各種《尚書》版本,真假難辨、可信度大失。
我們今天談論大禹,並非“信而好古”,更非“厚古薄今”,而是實事求是地對待祖宗先人,激發民族自尊心,引出對今人的啟迪。